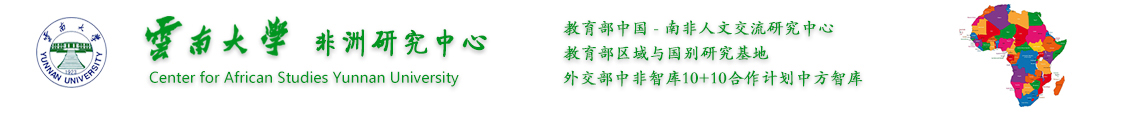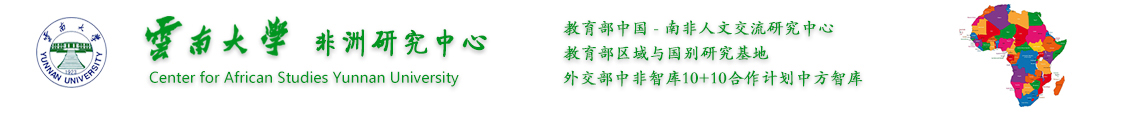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国际制裁与非洲”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11月5日在云南大学召开,这是构建更为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系列研讨会第五场研讨会。研讨会围绕“国际制裁的理论探讨”和“国际制裁的案例分析”两个主题展开,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和云南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20余人出席研讨会。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党委书记、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永宏研究员在开幕致辞中重点介绍了云南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研究建设的现状以及未来重点方向,期待与会专家的更大支持;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春研究员主持会议开幕式并作会议总结。现将会议相关讨论总结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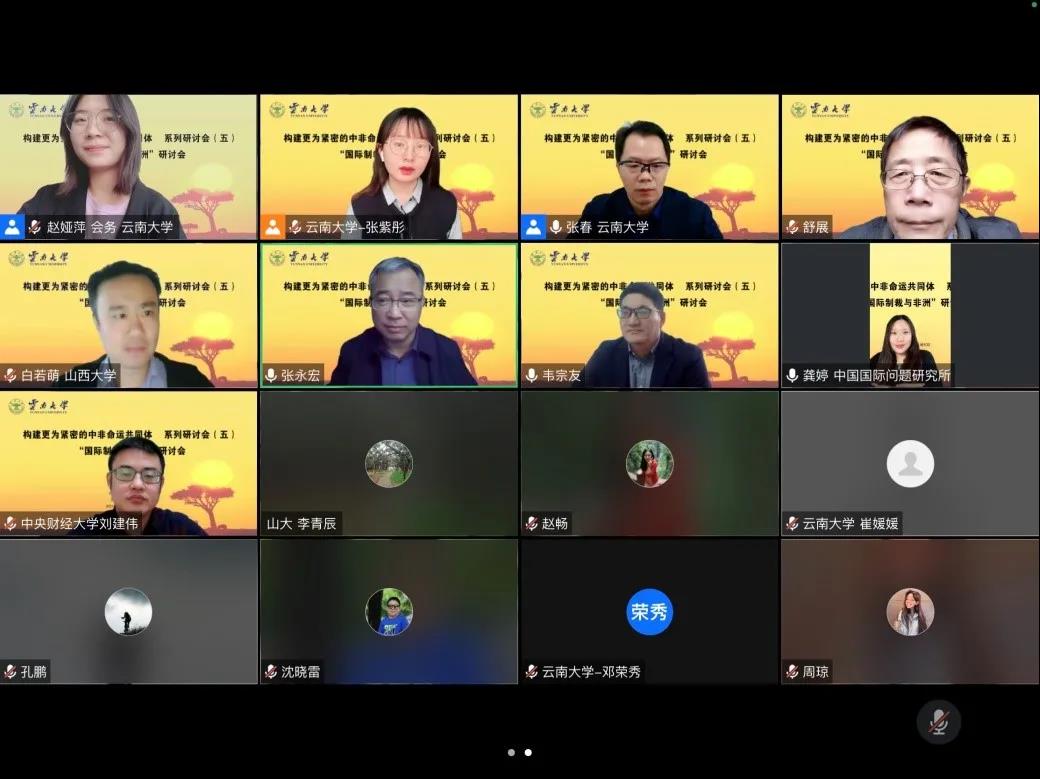
一、国际制裁的理论探讨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韦宗友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龚婷副研究员及中央财经大学刘建伟副教授等重点围绕“国际制裁的理论探讨”展开讨论。
韦宗友研究员重点探讨了制裁的概念、原因、逻辑、作用条件、类型以及合法性等基本理论问题。韦宗友研究员认为,国际制裁现象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存在,并在冷战结束之后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从概念上看,国际制裁是指针对未能遵守国际标准、国际义务或国际法的对象国,发起国通过威胁或实施惩罚的后果迫使前者做出特定政策和行为改变的外交手段。制裁区别于高成本的战争手段和效果有限的经济奖励;通过辅之以制裁这一类的“大棒”政策可以迫使对象国纠正错误。国际制裁一般包括单边制裁和由国际组织授权的多边制裁,前者主要是一国对另一国的惩戒行动,很多时候本质上是权力政治,后者则主要是为了捍卫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通常具备合法性。整体上看,获得国际社会公认国际组织认可的制裁具备合法性,而单边制裁则总体位于灰色地带,多数国际法学者认为其属于强权政治的表现。另外,制裁的方式包括全面制裁和聪明制裁,制裁措施有经济、外交与政治之分。制裁主要基于收益—成本分析的理性逻辑,具备两种传导方式,即针对被制裁国的领导人和内部其他政治团体、精英。20世纪80年代以前,普遍认为制裁效果较差,但此后尤其是南非结束了种族隔离政策之后,学者倾向于认为制裁有效。可以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相互依赖、冷战后和平发展时代主题、冷战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等发展,是国际制裁得以发挥效用的重要条件。
龚婷副研究员重点分析了美国单边制裁的理论、制裁决策形成以及反制裁动向等议题。龚婷副研究员指出,从决策行为体来看,行政部门在美国制裁政策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国会相关立法最初更多是为了限制行政部门发起制裁的权力,但在实际应对制裁问题中美国国会往往与行政部门保持很大程度的一致。但由于制裁会伤害到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甚至是第三方的利益,因此利益集团因此常常游说政府要求减少制裁的外部性并使得制裁更加精准。此外,制裁的影响与被制裁国家的国力相联系,制裁更能够作用于小国或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而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裁更多是在传递一种信号,而非为目标国带来实质意义上的政治和经济损害。龚婷副研究员深入分析了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的制裁决策变化。特朗普总统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历任总统中最偏好制裁的领导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特朗普政府团队热衷于“经济战”,偏好运用制裁这一外交工具维护美国国家安全;这期间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在制裁问题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工商界利益集团等越来越倾向在人权、价值观等问题上发声,主张接触的金融利益集团在特朗普政府中决策影响力不断下降,其游说的意愿和能力都有所变化。拜登政府近期完成了对美国制裁政策的评估,其在制裁问题上的偏好未呈现出实质性变化。龚婷副研究员还对反制裁问题进行了探讨。她指出,近些年国际社会反制裁政治力量不断扩大,去美元化探索进一步发展,反制裁国际合作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期;同时,中国的反制裁能力建设也壮大了全球反制裁力量。
刘建伟副教授聚焦美欧经济制裁合作。他指出,狭义上的经济制裁指主权国家为了实现特定的对外政策目的,对本国与他国的经济往来施加限制的做法,具备三个特征:主权国家是实施主体、高政治的目标以及经济上的限制措施。就相关研究来看,刘建伟副教授认为,此前研究存在经济制裁界定过于宽泛、数据不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强化定量研究。刘建伟副教授统计了冷战后(1993/11/01-2019/12/31)美国和欧盟发起的单边经济制裁的情况,并围绕美国对外政策以及承诺提出了影响美欧经济合作的四个假设:一,当美国对外政策为多边主义时,双方合作水平高;二,当美国制裁政策与联合国政策一致时,美国越容易获得欧盟的配合;三,当美国自我施加的经济成本高时,欧盟配合会增加;四,随着欧盟对外制裁制度更加完善时,欧盟参与美国制裁的频数增加。其中,第一、第二和第四个假设都得到数据验证,第三个假设则没有得到验证。
二、国际制裁的案例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杨宝荣研究员、政治研究室沈晓雷副研究员,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若萌博士,及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赵娅萍等重点探讨了“国际制裁与非洲案例”。
杨宝荣研究员围绕制裁性质、如何看待欧美制裁以及中非如何合作解决非洲因制裁带来的问题进行了发言。杨宝荣研究员认为,制裁是一种外交手段,反应了制裁发起方的制度理念和背后的发展路径。在当前美国OFAC的制裁项目中,37项中有10项涉及非洲,另外还有一项钻石出口贸易制裁涉及非洲。津巴布韦因为土地问题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毫无疑问,土地问题是制约许多非洲国家包容性、可持续性增长的重要阻碍,但是以西方价值观去看待南非、津巴布韦的土地问题改革肯定存在问题,即没有尊重非洲主权国家在利用自己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制裁在客观上是强加的。杨宝荣研究员指出,美国对外制裁的标准是自身价值观和维护自身利益。由此,在制裁过程中凸显严重的双重标准问题。针对美国有专门针对中国军工企业和新疆问题的两项制裁,杨宝荣研究员认为,制裁研究不能跟随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国发展的成效成就了中国教科书式的发展经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要用中国的立场和原则来看待制裁问题。在对外合作中,应该秉持支持发展中国家按照自己的历史条件来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制度设计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沈晓雷副研究员着重分析了西方对津巴布韦制裁的基本情况、制裁原因及后果。西方于2002年初开始制裁津巴布韦。最早的启动对津巴布韦制裁的是欧盟,制裁内容主要包括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冻结资产,对象是穆加贝总统和19名政府和军队高官。2002年2月22日美国也开始制裁津巴布韦,目标有19个个人,其法律依据是2001年《津巴布韦民主与经济恢复法案》;2003年3月6日布什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对77名高官进行制裁。此后,美国几乎在每年都会重新审议对津巴布韦的制裁。除美国和欧盟外,英国、瑞士、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等国家也基本上从2002年开始制裁津巴布韦。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的制裁一直持续至今,其力度经历了一个先升高再下降的倒V字。西方国家制裁津巴布韦的原因主要包括西方国家对2000年穆加贝总统的快车道土地改革和2002年津巴布韦总统选举不满。2000年欧洲议会通过了针对津巴布韦土改的决议,认为穆加贝政府占领农场违反了人权法制,呼吁津巴布韦在民主、非暴力基础上进行土改;2001年12月,欧洲议会呼吁理事会进行聪明制裁。美国也在2001年通过法律,要求津巴布韦进行透明合法的土改。另外一个更为直接且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尤其是2002年总统选举发挥了导火索的作用。就制裁的影响来看,制裁对津巴布韦经济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政府甚至将其视为2000年后社会和经济危机的最主要原因。目前没有具体的数据来表明制裁对津巴布韦造成的损失。此外制裁也有着严重的社会影响。
白若萌博士深入讨论了美国对非制裁的性质、制裁的力度以及制裁决策制定。他认为,美国对非制裁的目的既有政治的也有非政治的,其中民主是最主要的制裁要求,具体包括重新举行选举、修改选举法、要求国际观察团进入选举等。制裁的力度取决于被制裁国破坏政治秩序的程度,具体包括选举舞弊、篡改宪法、军事政变、镇压民众四个层次。一般而言破坏层次越高,制裁力度越大,因此,对外制裁的力度包括从低到高的零制裁(空头制裁)、弱制裁、援助制裁、军事制裁、金融制裁五个层次。前四个层次只是切断了双方的交流,而最后一个层次表明制裁进入实施。整体上制裁的力度取决于破坏政治秩序的烈度。而制裁决策主要涉及到认知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或成本收益分析。
赵娅萍探究了美国国会出台对非制裁法律的重要条件。美国的制裁决策主要涉及总统和国会两个首要的决策行为体;近年来美国制裁政策表现出两大特征:国会愈发成为美国制裁政策的主要推动力、撒哈拉以南非洲已经成为美国首要的制裁对象;根据全球制裁数据库的统计,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已经成为美国最首要的制裁对象,占到美国对外制裁比重的41%以上。因此,通过搜集国会自1975年至2018年的制裁立法,并运用逻辑回归的方法,该研究发现国会制裁存在明显的非军事议题导向,同时民主党意识形态以及国会团结都会增加国会的制裁动机,而紧张的府会关系以及盟友关系则会导致国会制裁行为的减少。